胡佳琦
中秋時節,天上月圓、人間團圓是刻在中國人骨子里的文化記憶,是跨越山海也要奔赴的溫暖約定。
本期書單以“團圓”為脈絡,串起五部飽含鄉情與親情的文學經典。中秋過后,愿您繼續與好書相伴,透過文字跨越時空,在月光下品味人間至情,在閱讀中感受家的溫馨。
家人閑坐,燈火可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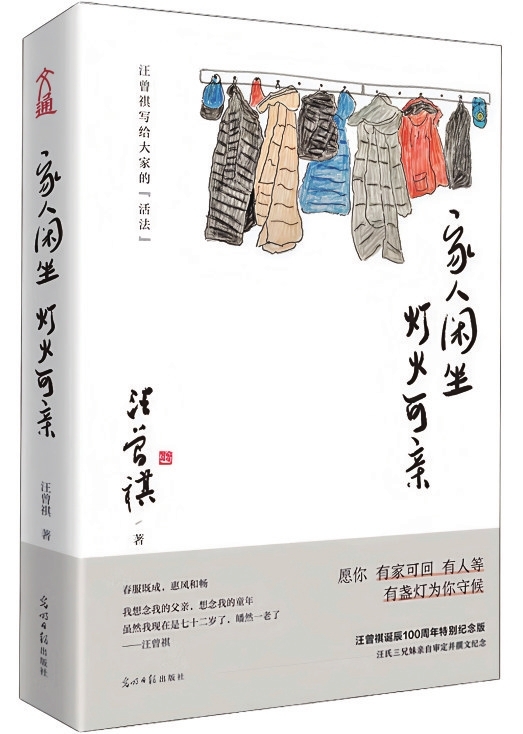
人間至味是清歡,燈火可親即團圓。真正的團圓,往往藏匿于最平常的一日三餐、家人閑坐之中。汪曾祺的散文,便十分擅長捕捉這份俗世生活的暖意。
他的世界里,家從來不是華麗的舞臺,而是煙火氣繚繞的廚房、閑話家常的庭院和燈盞下圍坐的夜晚。在《家人閑坐 燈火可親》中,他寫父親釀酒、母親做菜、兄弟姐妹拌嘴,寫故鄉高郵的端午鴨蛋、昆明雨季的菌子、北京冬天的白菜。這些尋常物事,因有了人的溫度,便成了“家”的符號。
他筆下的團圓是日常中的相守。一句“家人閑坐,燈火可親”,道盡了中國人對生活最樸素的向往。即便是在物資匱乏的年代,一碗熱湯、一碟小菜、幾句閑聊,也能讓生活有滋有味。讀汪曾祺,仿佛回到那個沒有手機、沒有紛擾的夜晚,一家人圍坐燈下,話雖不多,心卻貼得最近。
湘西一夢,守望成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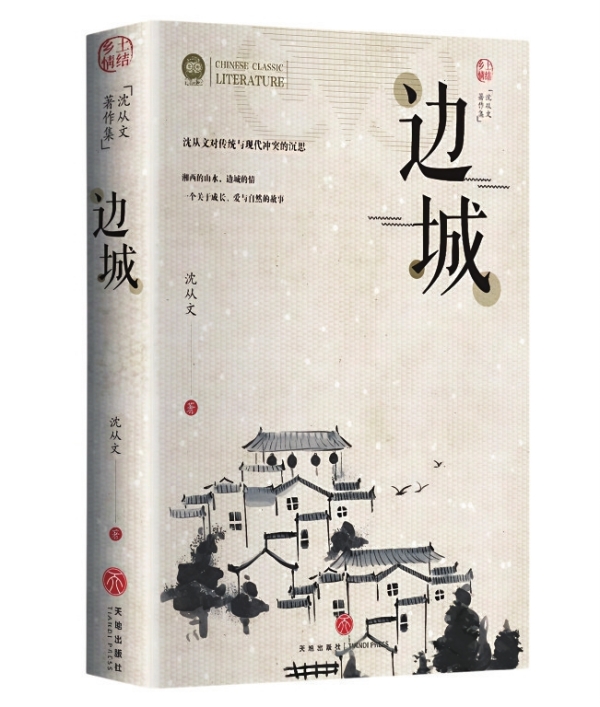
湘西的茶峒,青山環抱,綠水長流,這里有著最樸素的人情和最溫暖的守望。
沈從文的《邊城》,講述的是一個關于等待的故事。在茶峒,少女翠翠與爺爺相依為命,擺渡為生。她的愛情如白塔下的溪水,清澈卻曲折。爺爺去世后,翠翠依然守在渡口,等著那個“也許明天回來,也許永遠不回來”的人。每逢端午,龍舟競渡,人群歡騰,卻是翠翠最孤單的時刻——她所期盼的那份團圓,總是在咫尺天涯間擦肩而過。
這本書里沒有大團圓的結局,卻蘊含著中國人對團圓最深的執念。翠翠的等待,是對承諾的堅守、對緣分的信任。沈從文以詩意的筆觸,將邊城的山、水、人、情融為一體,讓讀者在淡淡的憂傷中,感受到一種超越時空的溫柔力量——縱使人難團圓,心卻始終相連。這份無盡的等待,雖帶著哀傷,卻也閃爍著希望的微光,成為另一種對團圓的長久期許。
漂泊何處是歸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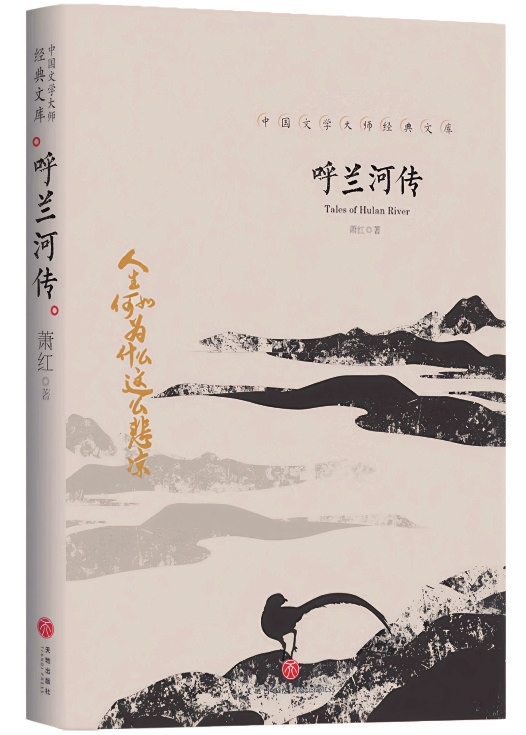
并非所有的團圓都能如愿。有時,離別是常態,思念便成了另一種形式的精神歸鄉。蕭紅的《呼蘭河傳》,便是作者在顛沛流離的晚年,對故鄉與童年進行的深情懷想。那座東北小城里,有她童年的后花園,有慈愛的祖父,有那些看似愚昧卻鮮活的生命。這一切,構成了她生命中最初,也是最終的精神原鄉。
書中對團圓場景的直接著墨或許不多,但通篇都浸透著對“家”的渴望與追憶。那一次次熱鬧的放河燈、逛娘娘廟會,又何嘗不是一種集體性的、對平安團圓的樸素祈愿?
該書真實再現了20世紀初中國東北小城的風土人情。盡管書中不乏對愚昧習俗的批判,但字里行間更重的,是對祖父、對后花園、對故鄉煙火的深切眷戀。當作者漂泊至異鄉,于病榻上回首往事時,這座用文字重建的“呼蘭河城”,便成了她靈魂最終的棲所,是一幅永不褪色的團圓圖景。
城南往事,童真不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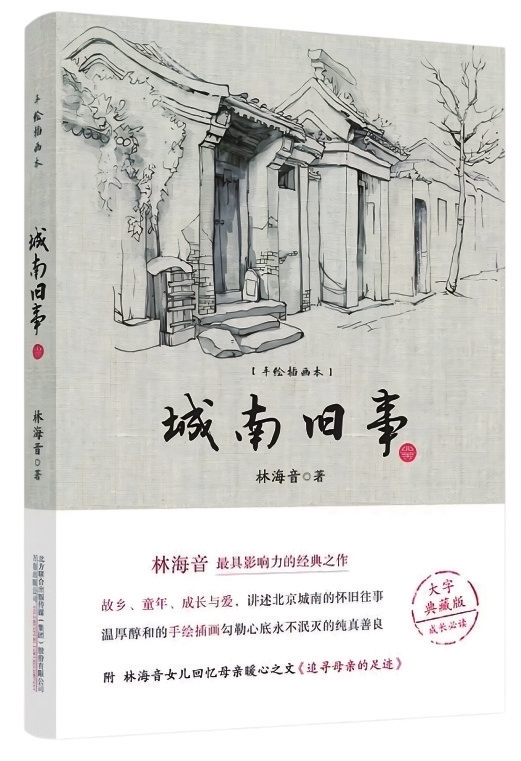
城南的胡同里,駝鈴聲聲,小英子的童年充滿了別離,也寫滿了團圓。
林海音的《城南舊事》,通過小女孩英子的眼睛,再現了老北京城南的人情風物。她寫惠安館的秀貞、草叢里的小偷、蘭姨娘與德先叔以及宋媽與她的兒女……每一個故事都帶著淡淡的離別,卻也藏著深深的溫情。英子不懂成人的世界為何總有無奈,但她始終用一顆純凈的心,去理解、去接納、去告別。
林海音并不渲染悲傷,而是以細膩克制的筆調,書寫生命中的相遇與珍惜。“爸爸的花兒落了,我也不再是小孩子。”所有的離別匯聚于此,童年就此落幕。然而,當她多年后回望這段歲月,那些逝去的人、遠去的事,都在文字中重新變得鮮活。即便有些人注定要走散,那些共同擁有的時光,依然如城南的斜陽,溫暖而明亮。讀罷掩卷,仿佛也跟隨著英子的腳步,在胡同深處,完成了一次與童年時光的重逢。
此心安處是吾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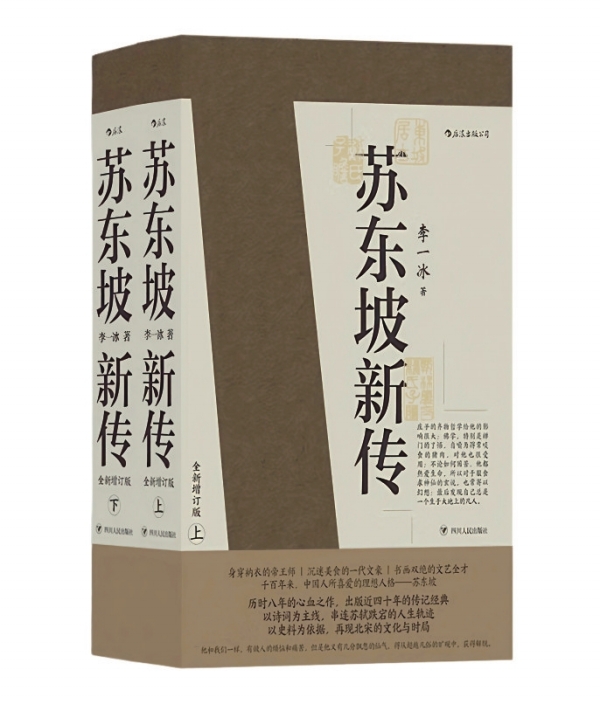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蘇軾一生顛沛流離,卻總能在漂泊中安頓身心。
《蘇東坡新傳》以細膩筆觸勾勒這位文學巨匠的生命軌跡。作者李一冰查閱大量史料,耗時多年精心打磨,生動再現蘇軾在政治風波中的沉浮,并聚焦于他與弟弟蘇轍的手足情深。書中展現了二人在中秋夜“但愿人長久,千里共嬋娟”的相互寄懷,以及晚年相約歸隱的約定。
盡管命運多舛,蘇軾始終以豁達胸懷面對人生際遇。他在黃州躬耕東坡,寫下《赤壁賦》;至惠州便“日啖荔枝三百顆”;及儋州則辦學育人,傳播中原文化。他將每一次貶謫都當作深入民間、體驗生活的機會。他交友、品美食、品茶、創作,將困苦的生活過得生趣盎然。“試問嶺南應不好,卻道:此心安處是吾鄉。”這種強大的精神力量,使他無論身處何地,都能保持內心的曠達,與困境和解,與所熱愛的文化傳統緊密相連,實現了個體與命運、與文化的團圓。
責編:劉茜
一審:劉茜
二審:印奕帆
三審:譚登
來源:華聲在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