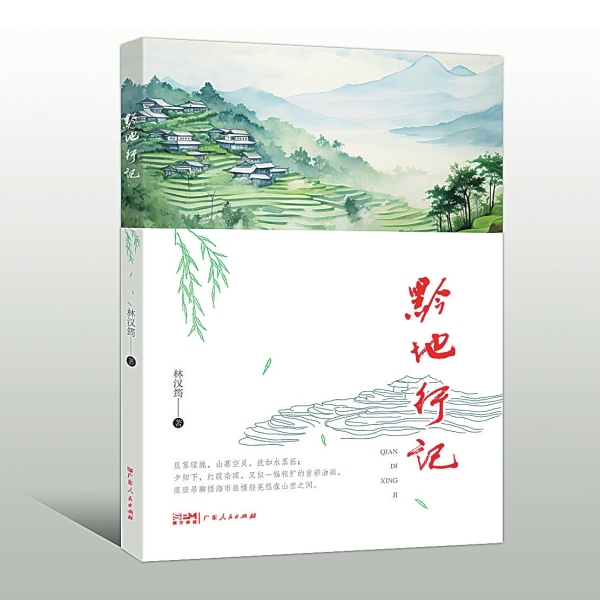
粟立新
湘籍作家林漢筠新近出版的文化散文集《黔地行記》,是他赴黔為期半年的東西部協作“文化交流”而衍生出來的副產品,通過“那山”“那水”“那人”三個章節,進行一場湘黔兩地的精神對話。
“霸蠻”,是湖南人的口頭禪,是刻進骨子里的文化基因。這種湖湘的精神特質,如同一條隱秘的河流,始終流淌在林漢筠的文字里,即便落筆于他鄉黔地的山水自然與人文歷史,也難掩其湘人“蠻味”本色。在寫位于德江縣平原鎮的中共黔北工委時,他避開宏大敘事與歷史事件的平鋪直敘,以湘籍先輩宋至平(中共黔北工委創辦者之一)的足跡為引,創作出《宋至平的十字關》。作家筆下的“十字關”,讓歷史人物的抉擇與地域文化基因緊密相融。它既是平原的一個重要路標,更是宋至平以及像宋至平一樣的革命者對革命信仰的堅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湘人“霸蠻”精神的延續和“經世致用”的傳統。
文廟,是地方的文化符號之一。黔地安化縣文廟與湖南安化文廟,在作者的筆下來了一次精神碰撞。看似兩個孤立的文化符號,成為湘黔兩地的文脈交融見證。飛檐斗拱間,有黔地的文化記憶與張揚,也倒映出湖湘文化“以文化人”的如磐初心。這種個人探討與文化尋根結合的寫法,蘊藏著歷史溫度。
《山祭》,講述的是三個寶慶人與一個黔地土家漢子的故事。寶慶人劉儀順在黔地與當地土家族人胡勝海結盟起義,湘軍將領、寶慶人席寶田揮師鎮壓起義軍,150年后“我”拜祭當年的戰場。作家以細膩的筆觸,把兩個地域的人、兩種文化的魂,悄悄焐在了一起,更是將這種湘人精神的書寫推向深處。他沒有回避歷史,而是在這種張力中,讓湘人“蠻”性的多面性愈發清晰。這里有黔地山民為生存而戰的悲壯,有湘籍將領為“平亂”而揮的刀劍,有湘人血脈中“揭竿而起”的抗爭本能,更有湖湘文化里“忠君報國”的傳統認知。
一個成熟的作家,首先是在尋找,尋找與自身文化記憶相呼應的符號,尋找故事力學的解構,再自覺不自覺地進行文化回溯。在《黔地行記》中,林漢筠有意無意地“植入”湘地文化,讓湘黔兩地文化在文字里對話、共鳴,形成獨特的“湘黔呼應”敘事結構。如《聽儺》,他將兩地民間文化進行比較。湘地長輩“抓力虎”戴著“木腦殼”的“架式”,與德江戴著儺面舞者的身影漸漸重疊,將筆觸深入“梅山教”與德江儺戲的精神內核,這種文化共鳴便愈發鮮明。無論是湘地梅山文化中的“趕尸”“放蠱”背后對生命力量的敬畏,還是德江儺戲“上刀山”“下火海”中對困境的抗爭,其本質都是對人性本真的堅守,而這份共通的精神內核,也讓兩個地域的文化有了溫暖的人性聯結。
作家還善于抓住方言與味覺這把鄉愁的鑰匙,用方言突出“蠻味”,用味覺具象“蠻味”。稱呼女性長輩的“嬢嬢”、樂器的“當當”、面具的“木腦殼”……鮮活的方言,像在異鄉突然瞥見故鄉熟悉的影子,讓人回味綿長。而對于味覺的記憶,也在他的筆下變得格外細膩。如《“熬熬茶”,孃孃的味道》,制茶時“木鏟攪拌時發出的沙沙聲”“文火慢熬時飄出的焦香”,這種味覺上的共鳴,讓“鄉愁”不再是抽象的情緒,而是可觸可感的溫度、可品嘗的味道。他對“熬熬茶”制作細節的執著,對原料、工藝的細致描摹,本質上是對湖南鄉土飲食記憶的復刻:因為熟悉故鄉“油茶”制作的每一道工序,所以才會對“熬熬茶”的制作格外敏感。這種從飲食切入的書寫,小人物小細節,卻為“蠻味”有了最生動的注腳。
半載黔行,終成作家的一生修行。林漢筠以湘人“蠻味”追尋跨越地域的精神對話,讓《黔地行記》超越文字,成為湘黔文脈交融的珍貴文本,亦是在新大眾文藝的浪潮中,作家對自身文化身份的堅定確認。
責編:劉茜
一審:劉茜
二審:印奕帆
三審:譚登
來源:華聲在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