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許苗苗。通訊員 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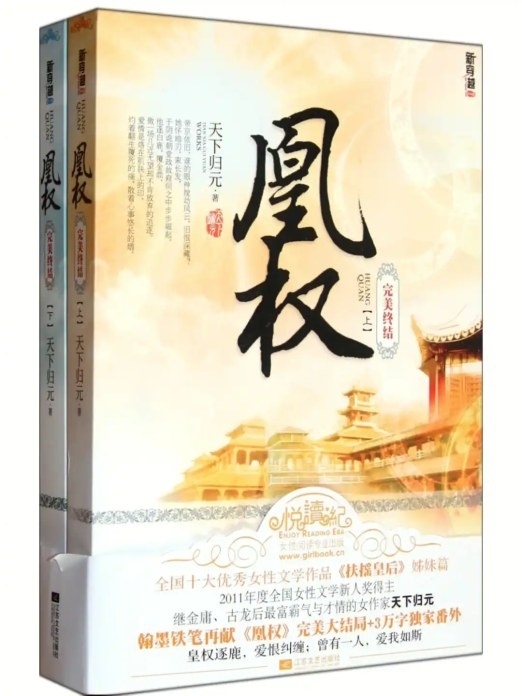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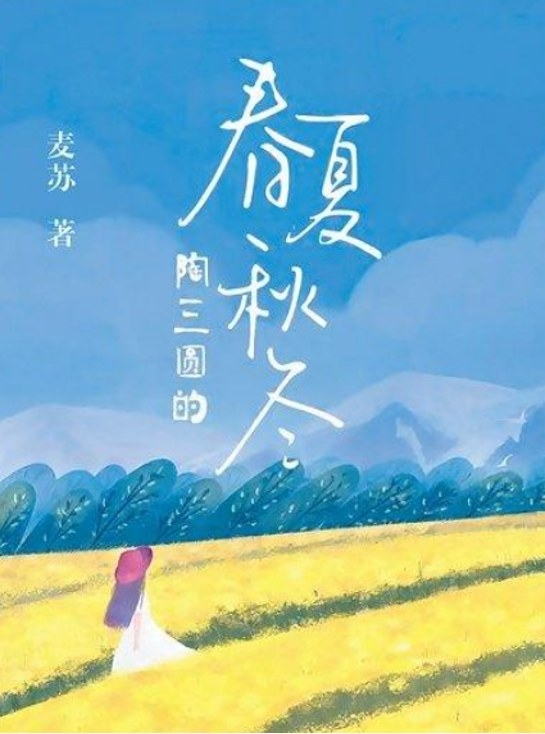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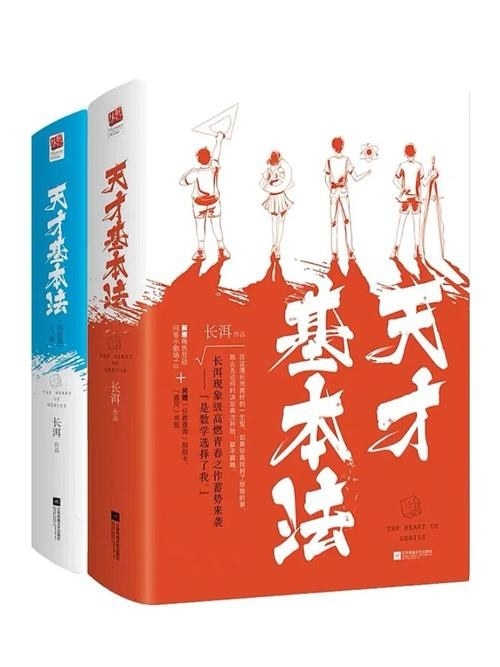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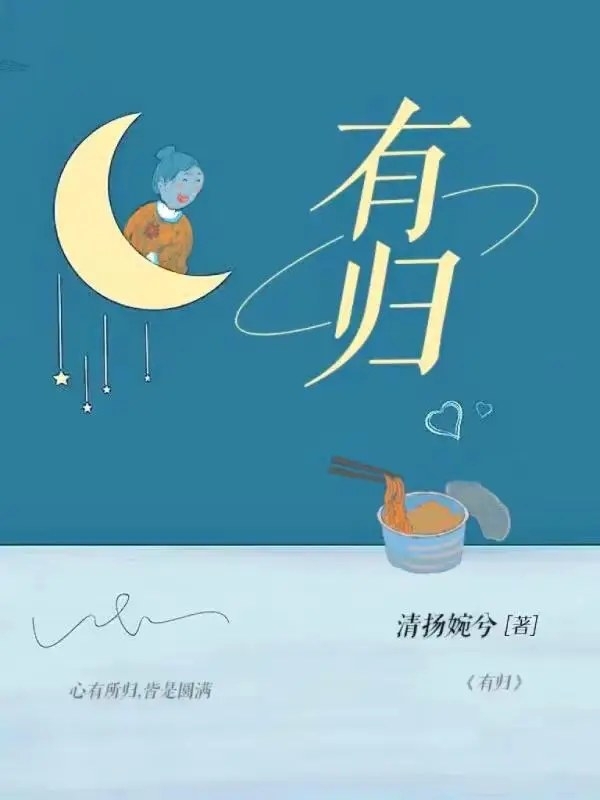
華聲在線全媒體記者 廖慧文
網絡文學是當前最熱門的大眾文化現象之一。6月17日,中國作協網絡文學中心發布的《2024中國網絡文學藍皮書》顯示,2024年,新增網絡文學作品200萬部,網絡文學用戶規模達5.75億。讀者性別結構均衡,男女比例相當。女頻(女生頻道)頭部付費閱讀平臺盈利能力穩步提升。
文學網站以性別分類作品,是其迥異于此前文學傳統的重要特征。近幾年,女頻網絡文學變化顯著,“女性成長”主題突破題材限制,從言情到懸疑、科幻、現實等題材全面開花,不斷拓寬邊界。
6月30日至7月4日,來自全國各地的80余名網絡女作家在長沙參加由全國婦聯、中國作家協會主辦的2025年全國網絡女作家培訓班。培訓班引導女作家深刻把握時代主題與創作方向,為她們的創作提供堅實的思想根基與創作遵循。
在業務技能培訓上,首都師范大學藝術與美育研究院教授許苗苗以“突破‘大女主’:網絡文學如何探索女性形象表達”為主題做了分享。她透過當下流行的網絡文學“大女主”人設的表象,從角色扁平化到人格多維化,從情感套路到女性形象塑造的方向深入剖析了網絡文學中女性形象書寫的困境與突破。
許苗苗已研究網絡文學20多年。20多年來,網絡文學發展迅速,自身概念、作品形式、文本對象等不斷發生變化,已經不限于當代文學、通俗小說、青年文化或亞文化領域。而其中“女性寫、寫女性”的網絡文學,反映出新讀寫方式對女性寫作的改造與促進。女頻的敘事也折射出女性現實的性別意識及變化著的情感模式和價值取向。
短而精,新時代女性作者優勢凸顯
湘江副刊:網絡文學分為女頻和男頻,但相較此前傳統書刊上的通俗文學和嚴肅文學,為何網絡文學會形成這樣鮮明的性別分野格局?
許苗苗:傳統通俗小說也有目標讀者,比如愛情小說主要面向女性,偵探破案主要面向男性。美國學者珍妮斯·拉德威在《閱讀浪漫小說》里就聊過女性讀者群體和女性作者之間怎樣互動、怎樣閱讀愛情小說。但嚴肅文學沒這么明確的市場定位。
網絡文學男頻女頻、男女讀者群分得特別清楚,因為其本質是商業化的通俗小說,得靠收費活下去。怎么掙錢?做市場細分。性別分野除了直接面向讀者市場,還方便作者和讀者互相找到,這其實就是靠興趣形成的“趣緣群體”。
雖說女頻文主打女性向,但作者肯定不拒絕男讀者,畢竟商業化寫作都希望更多人看、更多人買單。有意思的是,網上的作者和讀者不光通過文本聯系,還會形成情感聯結,比如“咱們都是女生,得互相支持”這種想法,慢慢就形成了有性別排他性的群體。所以有些作品雖說沒明著拒絕男性,但內容明顯更迎合女性,強化這種性別聯結。
湘江副刊:網絡空間對于女性寫作者意味著什么?是伍爾夫所說的“屬于自己的房間”嗎?女性網絡文學寫作的優勢在何處?
許苗苗:網絡空間確實給女性寫作者——其實也包括所有被傳統文學體制排除在外的人——打開了新天地。但就像前面說的,對那些專門寫給女性、討論鮮明女性話題的作品來說,網絡就像提供了一個“自己的房間”——一個獨立表達、相對平等的空間。女強(女性角色強大)文的平權想象,也可以看作伍爾夫“莎士比亞的妹妹”在網絡時代的舞臺。但商業化的女性寫作,更像是一個更大的平臺和機會,讓寫作能被更多人看到。
不過“女性作者”和“女頻”的概念不完全重合。特別是新時代女性網絡寫作,現實題材增加,關注領域更開闊,突破了類型限定。另外這些年來作協的扶植引導,對精品創作的鼓勵等措施,更注重選題和文學性,并不會刻意強調性別。
以前網絡文學靠類型化連載收費,得拼字數拼更新量。這種模式對男作者更有利,因為拼體力嘛。女作者普遍更講究文字質量,不太愛在篇幅上硬扛。到了新時代,網絡文學開始強調精品化,改編成影視劇的機會也多了,這時候女作者的優勢就顯出來了——她們寫的東西改劇本有優勢,搞精品化創作也更拿手,這兩點正好契合新時代網絡文學發展趨勢。
“大女主”是消費文化的產物
湘江副刊:女性故事常被認為是以浪漫愛情故事或家庭婚姻故事為主,現在女頻的核心敘事依然是言情嗎?當下的言情有什么新變化?
許苗苗:言情在女頻里還是主流,這可能也和女性本身情感更細膩有關系。但現在故事線拓展了,不像以前那么“死磕”感情線了。比如古代背景的有寫破案的、當廚娘的,現代的也有展現女性在各種行業里拼搏的故事。雖然多少還會帶點言情線索,但男主變成配角,給女主當事業搭檔或者助手。
湘江副刊:在女性主義的浪潮下,我們越來越多地聽到“大女主”等詞,伴隨而來的還有鑒定“大女主”的“真”與“偽”,您如何看待?如何看待對“嬌妻”的指責與對“愛女”簇擁?
許苗苗:網上發言挺容易情緒化的,有時候走極端。像說人家“嬌妻”“婚驢”,我不認同。日本學者上野千鶴子提出“厭女”概念,網上又對應著冒出“愛女”的說法,去年晉江文學城的熱文《女主對此感到厭煩》被看作“愛女文”代表。但其實這個概念并不清晰穩定,定義挺模糊的。
“大女主”說白了就是對理想女性形象的想象和期待,每個人想法都不一樣。“大女主”本質上是一個媒介和消費文化的概念。進入消費社會后,女性消費地位高,自然就冒出“大女主”這種迎合女性的形象。放到網絡文學里,表現得更放飛、更極端一些,就有了女強、女尊這些類型。
現在網上對“真大女主”“偽大女主”的爭論,大多是年輕讀者帶著情緒在辯,從學術角度看沒太大意義。這些概念跟女性經濟獨立脫不開關系——要是沒消費能力,誰會寫“大女主”來討好女性呢?
湘江副刊:很多女頻作品被影視化改編,一些作品的人設和價值觀在當時無爭議,但是改編播出后卻引起了很多爭議,您如何看待?
許苗苗:網絡文學改編影視劇容易引發爭議,說到底還是因為文字和影像壓根是兩碼事。小說能用文字慢慢鋪陳細節、深挖心理,但影視劇得靠強沖突、鮮明人設撐起來,就算網絡文學本身人設夠突出,文字里能寫的細膩層次,鏡頭語言也未必能全說清楚。
而且兩邊的受眾差異太大了:網絡文學讀者各有各的偏好點,可能沖著某個細節或人設追更,但影視化后得照顧大眾口味,小眾設定往往得改。比如天下歸元的《凰權》《辭天驕》《女帝本色》等,原著都是女主更強,但改編的劇版最后還是往“男皇女后”的傳統框架上靠了。
現實題材網絡文學開始往深處走
湘江副刊:您有印象深刻的令人耳目一新的女性角色和故事嗎?
許苗苗:讓人眼前一亮的女性角色不是那種從沒見過的全新設定,而是在大家熟悉的類型里玩出新花樣。
比如丁墨《烏云與皎月》的女主職業是網絡文學作者,丁墨把自己和身邊人的生活狀態融進去了,人物塑造得特別可愛。長洱《天才基本法》,女主靠重生加奧數比賽改命,人設和劇情都挺新鮮。
還有一些現實題材作品。比如麥蘇《陶三圓的春夏秋冬》,胖乎乎、樂呵呵的鄉村女孩陶三圓大專畢業后留在鄉村當“家里蹲”,憑借穩扎穩打、從容不迫的努力,成為了最年輕的村委會副主任。她是個真實自然的鄉村女孩,改變家鄉面貌的動力來自于對親人、伙伴的真實愛意,突出了個人與鄉土命運的共生關系,這種將個人與養育環境緊密聯系的寫作方式在女性文學中具有代表性,說明現實題材網絡文學開始往深處走。清揚婉兮《有歸》是一部描寫未婚未育高收入女子老年生活的現實題材小說,描寫出多樣化的老年女性生存狀態。現實題材要讓讀者看到自身閱歷之外真實的人生經驗,帶來一種新的生命體驗。女性作者比較敏感細膩,能夠對當下關注的現象、容易引爭議的話題給出多個視角的觀察。
湘江副刊:以前女頻流行的題材如宮斗和宅斗,現在沒落了嗎?
許苗苗:宮斗文這兩年不算沒落,但確實有變化。以前經典的像《后宮甄嬛傳》,一群女的圍著皇上轉;后來出了《宮墻柳》,畫風變成女性互助——皇上愛咋咋地,姐妹們互相幫襯著在宮里過日子,“歲月靜好”。
宅斗文也分化了,好多跟懸疑言情或者基建文結合起來,成為展開故事敘述的手法之一。還有這兩年流行的單元劇懸疑,像女仵作、女偵探、女殺手這類角色特別多,比如新出的《噓,祝娘子她又在和尸體對話了》,寫得還挺有意思的。
網絡文學也要追求“真善美”的文學精神
湘江副刊:現在有些網絡文學主角極端自私功利,您覺得弘揚真善美在網絡文學中過時了嗎?
許苗苗:真善美是永不過時的主題。之前有部作品創作手法優秀,但網上很多讀者覺得不舒服——穿越到古代的主角確實冷靜理智,絲毫沒有“戀愛腦”,但這種為錢、為自保、為達目的犧牲他人的功利化做法我不認可。人生的美妙在于不確定性,而不是像穿越者一樣走最短路徑通關。文學本該給人全新的生命體驗,而不是機械的選項。
湘江副刊:網絡文學具有強烈的互動性,有時候可被視為作者與讀者共創的文本,常以“爽”為要點,這是否會削弱作者的獨立性和文學性?
許苗苗:其實說到“爽文”,一般人先想到的都是男頻那種打怪升級的路子,結構和邏輯都比較單一。女頻里嚴格的“爽文”不算多,畢竟女性讀者對情感更講究細膩度。
互動性對網絡寫作確實有幫助。但成熟的作者不會被讀者帶著跑,作者動筆前就想清楚了“要講啥故事,寫給誰看”,只有那種短篇打賞定制的情況例外,比如知乎上有一類作者寫作過程中會征集讀者意見,比如問“女主和兩男主,你們更喜歡哪一對?”然后根據讀者意愿續寫情節。這并不是被讀者牽著走,想寫好需要很高的人氣和文字技巧,作者得有很強的控場能力才行。
互動性不會削弱作者的獨立性和文學性。既然選擇在網上寫,接受互動其實是件好事,能給作者提供更多思路,也多了和讀者溝通的機會。好的作者愿意直面讀者。
湘江副刊:您對女性作者的寫作還有什么建議?
許苗苗:關于寫作和形象塑造,我建議,想提升文學性就別老想著“我是女性作者,專門寫給女性看”,畢竟偉大的文學從來不是為了迎合某類人。要是想走市場化路線,尤其是精準戳中小眾網絡讀者的情緒點,那另說。但如果想成為出色的文學創作者,而不是單純的文化產品生產者,就別被性別標簽框住,可以突出女性獨特的觀察和感受力,但得讓這成為優勢,而不是限制。
應該為網絡文學獨立設立獎項
湘江副刊:目前學界重視對網絡文學的研究嗎?在當下的文學研究中占比如何?
許苗苗:網絡文學作為新興現象,變化太快了,現在的研究還遠遠不夠深入,有很多空白等著填補,特別歡迎年輕學者加入。在當下文學研究里,它占的分量不算重,但在網絡文化里,它可是核心——畢竟影視劇改編、周邊、二創這些,都是從網絡文學故事開始的。所以研究網絡文學得放到整個網絡文藝的大框架里看。
現在學界把網絡文學歸到通俗文學里,覺得它偏商品化、取悅大眾,對原創性要求沒那么高。這不是說故事抄襲,而是手法創新,畢竟太新、太陌生、挑戰大眾審美就沒法通俗了。
湘江副刊:現在很多傳統文學獎項增設了網絡文學賽道,評選標準和傳統獎項有差異嗎?網絡文學應該獨立設獎嗎?
許苗苗:差異挺大的。比如茅盾文學新人獎更看重故事精彩度、社會影響力和傳播力,而傳統文學獎更關注作品的原創性、藝術創新和文學性。網絡文學獎項確實需要單獨設立,畢竟它和嚴肅文學是兩碼事,沒法用同一套標準衡量。標準可以側重這些:和當下生活的結合度、故事吸引力、社會影響力,還有媒介特性(比如互動性、衍生能力),不像傳統文學只看文本本身。
湘江副刊:您之前提到要對網絡文學開展交叉學科研究,還需要哪些學科介入?
許苗苗:目前從文學學科來的基本是當代文學和文藝學學者,除此之外,還需要媒介文化和傳播學、文化產業等學者加入。特別是媒介的影響,對網絡文學太重要了,比如創作過程中的互動、一部作品在網頁和出書時的改名現象等,都和媒介特性有關,以前研究傳統文學可沒這么復雜。
責編:歐小雷
一審:歐小雷
二審:蔣俊
三審:譚登
來源:華聲在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