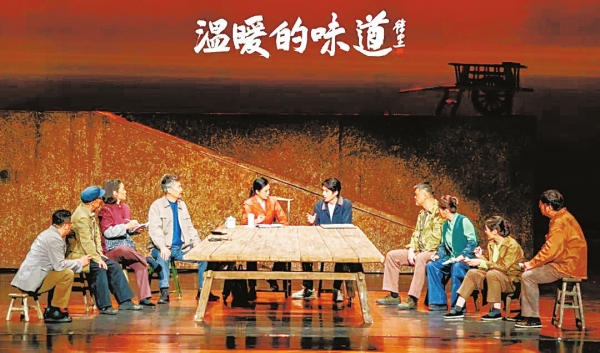
話劇《溫暖的味道》劇照。
劉月娥
在北緯37度的黃河岸畔,歷史悠久的“塬底下村”因為與赤道恰到好處的距離,成為孕育優質蘋果的沃土。這“合適的距離”,不僅是蘋果生長的黃金法則,更隱喻了話劇《溫暖的味道》的核心命題:人與人、觀念與觀念之間,如何找到那份恰如其分的“溫熱帶”。
作為一部現實主義力作,《溫暖的味道》將鏡頭對準了鄉村振興這場深刻變革。其核心沖突,是守護土地的老輩農民與現代知識青年之間觀念的激烈碰撞。四十年前,為擺脫貧困,村民們毅然去塬上開荒,種出了黃河邊上第一批蘋果。四十年后,塬底下村村民卻因蘋果歉收,漸漸對種蘋果失去信心。駐村第一書記、農業學博士孫光明(劉昊然 飾),懷揣新技術與新品種,回到闊別二十載的故鄉,面對的卻是鄉親們對幾近絕產的三十年老蘋果樹的固執堅守。老一代村民在傳統農耕文明中掙扎,新一代青年在科技浪潮中突圍,通過四十年蘋果種植史的興衰,該劇編織出一幅鄉村振興的壯闊圖景。
情與理的博弈構成了戲劇張力的核心。劇中的新時代女性郝鳳仙,堅強隱忍、突破性別藩籬,曾以“鋼鐵手腕”收回稅款、贏得多項榮譽。她以強悍果敢打破了鄉村陳規,但其信奉的“人情社會潛規則”讓她栽了跟頭。面對鄰村為一己私利發射“驅云防雹”炮彈,導致塬底下村遭受嚴重冰雹災害的行為,她情愿選擇私下和談,不要撕破臉,但無形中助長了對方的戾氣,導致了鄰村三年來的持續破壞。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新任駐村第一書記孫光明,他主張依法懲處鄰村的惡行。人情世故這把雙刃劍,在此刻展現出它的兩面性。郝鳳仙基于“人情世故”的權衡與孫光明堅持“依法治理”的立場,構成了全劇最核心的戲劇沖突。最終因為對鄉土那份共同的赤誠之心,他們之間的沖突消融。
《溫暖的味道》雖劇情質樸,卻蘊含著深刻的哲學思辨。劇中蘋果的意象被賦予了多重象征意義。新品種蘋果的培育成功,正如新思想在鄉村的扎根,需要“合適的距離”——北緯37度獨特的光熱條件。這“距離”的淺層含義是地理緯度,深層隱喻則是人際關系的親疏分寸。孫光明與郝鳳仙的沖突,緣于生存環境造就的觀念差異;老輩經驗與青年創新的碰撞,呼喚著人們用發展的眼光看世界。劇名“溫暖的味道”更耐人尋味。郝鳳仙為維系鄰里表面和氣而選擇隱忍,這是她的“溫度”;孫光明在情與法之間,理解、尊重郝鳳仙為村莊付出的三十年心血,依然以合情合法手段讓村民獲得應有的賠償,這是他的“溫度”。
那么,何為合適的“溫度”與“距離”?話劇并未給出標準答案,而是以孫光明意味深長的話語留給觀眾無盡思考:人與人的距離,如同蘋果樹與赤道的距離。過度的親近,可能導致“審美疲勞”甚至毀滅;過度的疏遠,則無法建立深度鏈接。世間美感與深度關系,往往存在于一種克制的“合適刻度”之中。孫光明面對郝鳳仙與村民的強烈反對,所保持的那份克制,正是在等待新事物破土而出的時機。最終,郝鳳仙從省農研所帶回新品種,孫光明帶來的新苗開花結果。這恰恰是等待與克制中醞釀出的“溫暖味道”。“溫度”在合適的距離中產生,“味道”在必要的克制中釀成。世事人情,莫不如是。
盡管話劇寄寓希望,但它也如實地映照出當下鄉村的困境。劇中人對昔日“溫暖味道”的深深懷念,蘊含著強烈的尋根意識與鄉愁。一位村民哭訴:“以前有男人放鞭炮,現在,人都沒幾個,守著幾棵老樹。”孫光明說:“小時候只要敲開門,就會有熱乎乎的飯。”這片用紅棗和小米養育他的地方,承載著人們對鄉村的共同回憶,和對心底那份溫暖的追尋。
正如中國藝術研究院話劇研究所宋保珍教授所言:“經常看戲劇的人不易得抑郁癥。”戲劇的療愈性,正在于觀眾在觀演中悄然代謝了心靈的淤積。《溫暖的味道》便是這樣一部作品,它借助藝術的內省之光,引導我們理解生活的復雜,撫平不如意帶來的創痕,在戲中尋找真實的自我,達到心靈的療愈。
責編:歐小雷
一審:歐小雷
二審:蔣俊
三審:譚登
來源:華聲在線








